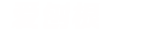说的比唱的好听
导读说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难得的精神盛宴跟演电影一样艺人进村就像过大年男人女人心里都是活泼的不再平静如水小孩子更是欢蹦乱跳兴奋得不能行我村偏僻但也有说书人游逛到这里
芭蕉雨声
听一回说书好比吃了一顿改样儿的好饭许是说书人与听者搭手一个烧火一个掌勺联合炮制出来一锅美味不然怎会两厢痴醉于同一物事说书的动静随童年收尾而日渐微弱终至寂无干预了本初的生命过程说书便镌刻在我的意识里久了沉淀为潜意识偶然打捞浮出心海仍铮亮如新平顶山马街书会即是带着三百里长把的铁钩年年在正月十三这天将我的旧梦钩住使我蠢蠢欲动且又仅至于此十年梦醒我跨过了黄河掠过几个高速路口而终达书会现场这是圆梦之行
正月十三日近惊蛰乍暖还寒但寒得底气不足薄袄不冷只是风大凌厉如鬼化为黄雾只往人群里钻应河水和绿麦苗都挡不住这股劲头说书人眉毛胡子头发一笼统听书人浑身上下驴打滚黄土地的黄呵让城里娇气的女子墨镜围巾伺候着仍灰头土脸愁眉不展说再不来马街书会了这话耳熟年年说年年人流如织乡人泼耐跟土亲张着大嘴手里的板子打得密不透风拉弦的闭目运气于双手弦外之音昭然一鼓作气气冲霄汉他必须撵着说书人的嘴跑说书的嘴也似被弦儿催着说彼此均不得松懈半分一曲终了戛然而止听书者大梦初醒一般叽叽咕咕议论一番久不愿散去大喊着再来一段是我恍惚了这是四十年前的情景那时的舞台不在平原不在麦地就在说书人脚下走过的村庄村庄的树下庙旁墙根儿或者牲口棚屋有时也在大队部视晴雨风雪而定
眼前的黄风中此起彼伏的坠子腔摄我心魄不由得拨开人堆挤到最前面一位身着半旧绿军装的老伯正说到紧要处右手的梆子噼里啪啦打得紧嘴薄眼细鸭舌帽似在说一段金戈铁马老故事他炸开双臂作拍马追赶状一旁穿黑棉袄的汉子弦乐跌宕紧追不舍这场景怎不让我跌落少年时那时候最常出没于我村的流浪艺人杨锁他住在另一个山坳的滑峪村把历史传奇编成坠子这村到那村不收费只为嘴说着说着就晌午或天黑了奶奶大娘们就端出饭来了他不挑食乡人也实诚我吃啥你吃啥杨锁单身三十多岁眼睛好腿不得劲扁平苍老的声音唯从他扁平的嘴巴才能发出说的那些小情小调我都记不得了但外地的流浪艺人比如浚县和兰考来的就技高一筹他们说长篇连载一说三四天十天半个月这村说罢换一个村说说到节骨眼上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吊俺的胃口喝他的清茶罗成算卦呼延庆打擂刘公案段保清投亲秦琼卖马我们撵着说书人到麦窖再到碾盘沟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味道天天听也听不烦妹妹记忆强一段书她听一遍就会复述绘声绘色段保清投亲最让我铭心刻骨段保清被嫌贫爱富的老妇吊在屋梁上皮鞭蘸水往下楞楞读平声用力抽打之意只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书场唏嘘声今犹在耳
我那时醉心于读书学习做好学生常逼迫自己抵御大门外的说书声在屋里熬油点灯算方程式那次父亲从黑夜走进屋里劝我从煤油灯下撤离他把我举到椅子上越过众人头我看见说书人唾沫横飞梆子紧急顿觉父亲格外温和可亲跟平日做校长时很不一样杨锁光棍儿一辈子领养一个闺女现患偏瘫多年尚能顾住自己也该有七十岁了
说书一开始到今天都是草根民众自弹自唱的消遣方式和谋生手段起初是身体残弱者为了活命而四方游荡后因各种缘由而在某天集聚宝丰县马街村恣意开腔亮嗓宣泄生之艰辛颂赞德义仁善苦中作乐乐在一瞬为吸引更多艺高名人亲临现场晒书马街书会专门搭建高台打擂筛选书状元高台外麦地上应河岸边更多的是散兵游勇微若虫蚁的痴迷者风大听不清书的情节但他们专注执着倾心的姿态和神情让我震惊和敬佩他们手脚健康五官完好已不再把说书当成活命的营生而仅仅只是爱是痴是迷是愿意愿意打起简板敲响鼓皮拉动琴弦不顾风沙和饥渴放开嗓子去吼去唱去说去晾晒警世和劝诫退为次要次要深入人心反而滋润出一片祥和宁静的风水宝地
马街的说书人自己也不知书能说多远就像花朵不知自己能结多大的果他们不曾预料到能走过七百多年风雨一直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中去我也想不到儿时在简陋地场听到的坠子腔韵能把舞台铺排到广阔的麦田绿苗为毯穹顶为棚播散幽远并透彻寰宇是的土气即地气当平原成为舞台土味浓郁的民间小调注定将成长为世界大艺术
书会现场
倾情专注
【说的比唱的好听 浚县饭店村算卦联系电话】老少爷们儿齐聚麦地
推荐阅读
- 在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辞职怎么办
- 水晶虾抱蛋几天产虾
- 对口招生是啥意思 对口招生是啥意思专科
- 劳动者辞职后怎么要工资呢
- 初榨和特级初榨橄榄油区别 橄榄油特级初榨是最好的吗
- 沙俄是俄罗斯吗
- 水沫子和翡翠的区别图,什么是水沫子,和翡翠有什么区别?
- 朋友圈快手点赞的说说 点赞的说说 朋友圈
- 母画眉鸟叫声30分钟,一个半小时是多少分钟呀?有人说30分钟,有的说90分钟,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