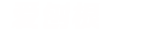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咖啡馆,将一楼变成《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 。那是欧洲最灿烂的时刻,人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的未来 。但谁也没想到,阴霾已经降临大地 。1914年,一战爆发 。
一战期间,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 。1917年,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 。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一词 。次年,阿波利奈尔病逝 。
这时的花神并不完美,但一战前的巴黎,也许才代表着巴黎最辉煌的时代,代表着欧洲乃至世界最辉煌的时代 。
传奇不灭,只是所托非人如今走入花神咖啡馆,仍可见到旧时形貌 。高靠背的卡座,低矮的木椅,深色隔板,米色墙身,还有金色围栏与马赛克地面……就连侍者们,都穿着与旧时一模一样的制服 。

文章插图
只是如今的座上客已非旧时人物,游客比例极高,朝圣一番,喝上一杯咖啡或一杯热朱古力,便寻找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隔壁的双叟 。
走上二楼,就会见到萨特与波伏瓦固定而坐的那张桌子 。波伏瓦在写作《第二性》期间,曾经写道:“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 。”
如今从二楼望下去,巴黎仍是那个巴黎 。只是,它早已不再是思想与文化的中心 。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竟无一选择法国之路 。巴黎依旧迷人,只是精英的幻灭感早已根深蒂固 。即使是辉煌的左岸,如今似乎也只有昔日荣光可以怀缅 。
塞纳河左岸是巴黎的荣耀,但最初的它并不属于巴黎 。严格来说,如今的第五区、第六区和第七区,在建成之初都不属于巴黎 。与之类似的是,如今艺术气息浓郁的蒙马特区,在建成之初也不属于巴黎 。
如果非要给左岸一个地理定义,那么应该是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一带 。巴黎最有名气的咖啡馆、书店、美术馆和博物馆集中于此 。
左岸的文化气息与右岸的商业气息截然不同,它没有浮华的那一面,它不是巴黎的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但却是巴黎的灵魂 。
有人曾经写道:“塞纳河是两个世界的天然边界 。它的右岸,是消遣、商业、奢华、新闻和演艺的巴黎;左岸则是思想、出版、大学、古董、书店的巴黎 。一个慌慌张张、急不可耐、躁动不安,另一个适合人们在咖啡座、书店和画廊里穿梭,或让人忍不住去塞纳河边的旧书店搜索一番……”
如果说左岸也有缺点,那么吃的太差或许是唯一 。我热爱法国菜,但唯一无法容忍的地方便是游客众多的巴黎左岸 。我甚至认为,左岸这些专做游客生意、价格也比周边高出一线的餐厅,大大败坏了人们对法国菜的印象——毕竟,对那些“来过首都就算来过一个国家”的游客来说,巴黎左岸是他们尝试法国菜的唯一机会 。可是当年,从美国来到巴黎的“迷惘的一代”,就是这样天天流连于左岸,不知道他们吃的法国菜,滋味是否与今天差不多 。
1903年,斯泰因来到巴黎,1939年,亨利·米勒离开,这三十多年便是“迷惘的一代”在巴黎的历程 。那时的巴黎和缓包容 。“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的扉页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